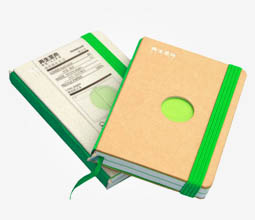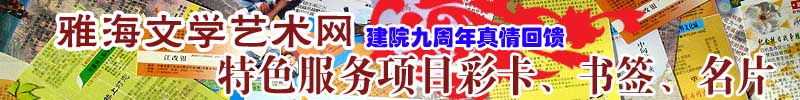北京市政府參事、垃圾對策專家王維平:垃圾分類別做環(huán)保秀!
和垃圾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王維平,對垃圾太熟悉了。從一個首都大醫(yī)院的醫(yī)生到一個中國最權(quán)威的垃圾專家,王維平用了20年,他所從事的垃圾對策研究和對拾荒大軍的調(diào)研,都是前無古人的事業(yè)。
1.跟蹤垃圾二十年,成為最權(quán)威的垃圾問題專家
“垃圾始終伴隨著人類,它見證了社會的興衰發(fā)展,也時常給我們帶來困擾、憂慮和啟發(fā)。如今,它已成為人類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可或缺的戰(zhàn)略資源。因此,它是一個既原始又現(xiàn)實的問題。但是我們對垃圾的認(rèn)識和研究仍不夠充分。我希望更多的卓越人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這是王維平不停強(qiáng)調(diào)的幾句話。
王維平最初的專業(yè)領(lǐng)域不是環(huán)境而是公共衛(wèi)生的醫(yī)學(xué)。他前后學(xué)了8年的醫(yī)學(xué),然后到北大一院當(dāng)了一名傳染病醫(yī)生——陽春白雪的職業(yè)。但是在行醫(yī)過程中,王維平接觸到了很多怪病,幾乎都難以治愈。例如“神經(jīng)脫殼癥”。“人的神經(jīng),除了中樞神經(jīng)之外都有殼膜,起到保護(hù)神經(jīng)的作用,神經(jīng)如果發(fā)生斷裂通過殼膜可以再生。“神經(jīng)脫殼癥”的表現(xiàn)就是所有神經(jīng)的殼膜都消失了。還有“口眼干燥綜合癥”——患者口和眼里都沒有了腺體,不能分泌淚水和唾液。“據(jù)我分析,這些怪病的產(chǎn)生皆源于環(huán)境問題。”
王維平意識到,治病首先應(yīng)該以預(yù)防為主,而自己的陽春白雪般的醫(yī)生職業(yè)只能坐等患者前來,但是類似的怪病根本無法治愈。所以,治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得病。此外,對王維平影響很大的要數(shù)東漢醫(yī)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書中言:“上醫(yī)治未病之病,中醫(yī)治將病之病,下醫(yī)治已病之病。”王維平將自己歸結(jié)到了下醫(yī)的行列:“如果不治理環(huán)境,那么我一輩子只能做一個下醫(yī),等著患者前來,告訴他他的病治不了。”
1986年,王維平毛遂自薦,到了北京市環(huán)境衛(wèi)生研究所,從主治醫(yī)師變成工程師。王維平認(rèn)為,不治環(huán)境的病,就治不了人的病。環(huán)境病中,垃圾為首。在當(dāng)時,王維平的決定令很多人不理解,從陽春白雪的醫(yī)生到與垃圾為伍,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
隔行如隔山,從公共衛(wèi)生轉(zhuǎn)向垃圾的王維平有些力不從心,但這卻激起了王維平的擰勁兒。為了更深地了解垃圾,王維平常常在周末,穿上破舊衣服,去和拾荒大軍一起撿垃圾、收廢品,到那些爬滿蚊蠅、老鼠的地方做調(diào)研,環(huán)境的惡劣難以想象。回來后,即使脫掉衣服還是一身的臭味兒。通過調(diào)研,王維平不但搞清楚了北京垃圾回收的全部過程和內(nèi)幕,還和以撿垃圾為生的人們交上了朋友,甚至和北京的13個拾荒大軍的“幫主”都結(jié)識了,他們尊稱王維平為大哥。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王維平也一起撿垃圾,吃蒼蠅飯,整天奔波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完全沒有了距離感。
經(jīng)過深入的調(diào)研,王維平1998年的《關(guān)于垃圾管理對策的調(diào)研報告》、1999年《北京垃圾回收及產(chǎn)業(yè)化調(diào)研報告》相繼問世,分別獲得了統(tǒng)戰(zhàn)系統(tǒng)的一個一等獎和一個二等獎。通過這兩個報告,王維平對垃圾從源頭到流散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了然于心,同時王維平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對拾荒大軍進(jìn)行調(diào)研的專家。報告一出,他便受到了國內(nèi)外的廣泛關(guān)注。王維平并未因此而自滿,而是在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和發(fā)達(dá)國家之間,在面對垃圾時還存在著很多差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92年,王維平自費遠(yuǎn)赴日本學(xué)習(xí)固廢處理和污水處理,歷時三年。王維平的父兄都居住在日本,有很多私產(chǎn)。當(dāng)王維平于早稻田大學(xué)畢業(yè)之時,家人對他進(jìn)行了百般挽留。從家里到成田機(jī)場,四個小時的路,風(fēng)燭殘年的老父親送了他一程又一程。“非要回去不可嗎?能不能不回去?”這是王維平的父親一路上說了不知多少遍的話,他希望兒子能夠留在他身邊,愛子之心,情真意切。王維平艱難地做了抉擇。“我學(xué)的專業(yè)是和環(huán)境有關(guān)的,中國的經(jīng)濟(jì)處于高速發(fā)展階段,在未來,城市環(huán)境問題亟待治理,只有在那里我才學(xué)有所用啊!”就這樣,王維平告別父親,回到國內(nèi),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對中國城市垃圾的實踐研究當(dāng)中。
從1987年到今天,王維平跟蹤生活垃圾已經(jīng)20余年,當(dāng)北京市垃圾的總體局勢明晰之后,王維平又開始關(guān)注廢舊輪胎和電子垃圾,王維平又分別跟蹤了六年和三年半。
無論是對生活垃圾還是廢舊輪胎,也包括電子垃圾的研究,王維平都是身體力行,而不是道聽途說。王維平研究的領(lǐng)域一直有人在研究,但是王維平所做的具體工作,在中國乃至世界從來都沒有人去做。
2.力倡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提出實在而操作性強(qiáng)的觀點
2005年北京“兩會”前夕,北京市政府邀請10位專家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王維平就是其中之一。當(dāng)時,王維平對市長王岐山說了25個字:“發(fā)展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節(jié)約型社會,提高增長質(zhì)量,降低發(fā)展成本。”
王維平是中國較早提出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理念、同時也是最早在中國進(jìn)行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可行性實證研究的專家。
1992年到1995年,王維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期間,親眼目睹了日本的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模式:資源—產(chǎn)品—資源再生的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比照中國,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卻持續(xù)著以消耗自然資源而謀求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歧路,即資源—產(chǎn)品—污染排放,最終必將造成資源枯竭、環(huán)境污染的惡性循環(huán)。在王維平眼里,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是抑制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唯一出路。
早在1994年奧地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出版《垃圾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同一年,王維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也出版了《垃圾經(jīng)濟(jì)學(xué)》一書,這是他在中國進(jìn)行垃圾跟蹤調(diào)研近10年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研究成果。
王維平總結(jié),中國現(xiàn)今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仍處在線性模式,在高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產(chǎn)生了大量的垃圾。根據(jù)物質(zhì)不滅定律,消耗多少資源就會產(chǎn)生多少垃圾,而產(chǎn)生的垃圾又千篇一律地采用填埋的方式進(jìn)行處理。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燒不勝燒、埋不勝埋的地步,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而且不利于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王維平在進(jìn)行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可行性實證研究的同時,總結(jié)出了推進(jìn)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實踐活動中必須把握的五大環(huán)節(jié),即:1、廢舊物資的有效回收系統(tǒng);2、規(guī)范的再制造業(yè);3、再生產(chǎn)品的市場培育;4、全面的質(zhì)量檢測、安全、標(biāo)準(zhǔn)體系;5、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規(guī)。
說起這五大環(huán)節(jié),王維平有些激動,噌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每列舉完一個環(huán)節(jié)便向門口移動一步,當(dāng)“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規(guī)”一條說完時,王維平已經(jīng)快走到了門外。“這五大環(huán)節(jié),完全是我通過實踐研究而得出的,在中國有很大的指導(dǎo)作用和現(xiàn)實意義。”站在門口的王維平,揮舞著雙手,慷慨激昂。那一刻,和共和國同齡的王維平對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的倡導(dǎo)和鐘愛溢于言表,他真正站在了垃圾學(xué)問的巔峰。在中國,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yè)。
因為在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研究上的建樹,今年5月9日至21日,王維平受美國安那波利斯市市政府、美國KCI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學(xué)和馬里蘭州議會(眾議院)的邀請,遠(yuǎn)赴美國就生活垃圾的管理、有關(guān)技術(shù)和環(huán)境問題進(jìn)行了交流考察。在會晤美國總統(tǒng)競選人希拉里夫人時,王維平談了中國的垃圾對策,得到了國外專家的普遍認(rèn)可。希拉里說,我們可以不研究飛機(jī),但不能回避垃圾。可見,垃圾處理、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早已成為世界普遍認(rèn)同的民生問題。
王維平的《中國城市垃圾對策研究》和《關(guān)于中國城市垃圾產(chǎn)業(yè)的調(diào)查研究》已經(jīng)被刊載入國務(wù)院2000年的《中國國情報告》。99世界管理大會發(fā)表論文《中國實行綠色會計制度的探討》,翌年,王維平又發(fā)表《中國應(yīng)實行綠色GDP制度》,并形成了中國致公黨中央提案。在中國召開的世界環(huán)境會計大會上,王維平提出了綠色GDP要建立在環(huán)境會計的基礎(chǔ)之上。2001年,財政部成立環(huán)境會計專業(yè)委員會,任命王維平為第一副主任。王維平隨即提出了修改現(xiàn)行經(jīng)濟(jì)核算體系,建立以綠色GDP為核心的新的國民經(jīng)濟(jì)核算體系建議。
王維平的建議都是產(chǎn)生于深入第一線的基礎(chǔ)上,按王維平自己的話說,因為實踐,所以我的觀點實在;因為實踐,所以操作性強(qiáng);這么多年我通過實踐得到的這些發(fā)現(xiàn),也是對社會進(jìn)步的一個推動。
3.“我?guī)У牟┦可±鴪觥?
王維平的社會頭銜很多,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的高級工程師、中國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會常務(wù)理事,此外他還是中國人民大學(xué)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的兼職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每年他都帶一兩個博士生。作為他的博士生,有一個硬性規(guī)定,那就是必須住垃圾場,深入實踐。這令很多人難以理解。
“在眾多的環(huán)境問題中,垃圾對環(huán)境影響最大,最普遍,最不受重視,也最難解決。”王維平說道。
上世紀(jì)80年代末北京的垃圾圍城是個教訓(xùn),如果垃圾問題得不到徹底的治理,那么連帶的其它產(chǎn)業(yè)都將受牽連。垃圾問題如此重要,和它受到的關(guān)注程度卻嚴(yán)重脫節(jié)。在我國,沒有一所專門研究垃圾的大學(xué),大學(xué)里沒有一所有關(guān)于垃圾的專業(yè),沒有一個垃圾研究所……對此,王維平不無擔(dān)憂。王維平的擔(dān)憂也包含了當(dāng)今人們對垃圾問題的漠視,能深入實踐真正地了解垃圾的人寥寥無幾,更多的人都是紙上談兵,甚至連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
“2003年,黨中央國務(wù)院提出了大力發(fā)展"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在此之前有關(guān)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的論著少之又少。當(dāng)國家提倡以后,相關(guān)的文章鋪天蓋地,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抄國外的,對中國的實際根本起不到指導(dǎo)意義。”
研究垃圾問題,如果不深入實際,深入調(diào)研,所有的論文都是站不住腳的。“無論是博士還是專家,和拾荒大軍比起來,沒有任何的優(yōu)越之處。這些游離于人們視線之外的拾荒大軍在面對垃圾時遠(yuǎn)比躲在象牙塔里做學(xué)問的專家聰明得多。他們對垃圾的分類已經(jīng)到了科學(xué)的程度。他們用手一摸,便能分辨出垃圾的成分,在許多人眼里簡單的塑料,一經(jīng)他們的手便能分成幾十種甚至上百種。聚酯的、聚丙的、聚乙的、聚祿的,無色的、單色的、雙色的,硬塑、軟塑頃刻之間便分成幾十堆,那些專家在這方面行嗎?”
最初,讓弟子住垃圾場的要求并不被接受,但是當(dāng)深入調(diào)研之后他的學(xué)生都改變了最初的看法。如今已經(jīng)畢業(yè)在中日友好環(huán)境中心工作的李華友就曾是王維平的博士生,當(dāng)時他住在秦皇島的一個垃圾場。在垃圾場的一個辦公室里,周邊都是農(nóng)村,沒有旅館,到最近的汽車站也得走半個小時。
另一個博士生是剛剛畢業(yè)的李文東,最初他只是在圖書館里查資料,準(zhǔn)備畢業(yè)論文。經(jīng)歷了一段時間的盲目琢磨后,仍舊沒有思路。李文東研究的是農(nóng)村廢物的回收利用問題,他下農(nóng)村之后,先后跑了四趟。在河南,他看到造紙廠的下腳料變成肥料,在湖南看到牛糞被加工成顆粒回歸農(nóng)田……在實踐調(diào)研的基礎(chǔ)上,李文東知道了自己的論文該如何寫了。
“他們一開始不接受,覺得自己是博士,是陽春白雪。去垃圾場肯定會覺得臭氣熏天、不體面。不過,他們最終都發(fā)現(xiàn),學(xué)問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做。”王維平說。
和其他男同學(xué)相比,王維平的女弟子張越顯然受到了優(yōu)待,她可以不住垃圾場,但仍然要去調(diào)研。現(xiàn)在的張越已經(jīng)是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教師。師從王維平期間,張越跑了很多地方進(jìn)行調(diào)研,并寫出了一篇教育部優(yōu)秀論文。
王維平對于做學(xué)問總是一絲不茍,他始終認(rèn)為真正的學(xué)問來源于生活,來源于實踐。“我們要提倡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如果他們的理論不是來源于實踐,又不能被實踐印證,這樣的理論毫無價值。”這是王維平回答的關(guān)于讓自己的學(xué)生入住垃圾場的原因。
4.身體力行,引導(dǎo)拾荒大軍處理好垃圾
王維平傾盡心血的《中國城市垃圾對策研究》是他的代表作,王維平經(jīng)過了數(shù)十年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在中國可行性極強(qiáng)的垃圾對策,那就是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這使得中國應(yīng)對垃圾的對策開始由末端向源頭、從被動向主動、從無害化向減量化和資源化過渡。王維平努力推動了垃圾管理對策的革命性轉(zhuǎn)變。
一噸垃圾從扔出來到裝上垃圾車,再經(jīng)過運(yùn)輸?shù)竭_(dá)垃圾填埋場,其間的運(yùn)行成本是158元,北京市每年花在這上面的資金就至少7億元。
針對中國的城市垃圾,王維平提出了幾條行之有效的具體應(yīng)對策略:凈菜進(jìn)城、限制包裝、舊貨交易、廢品回收、垃圾分類,等等。這些措施都是應(yīng)對現(xiàn)今城市垃圾問題的有效措施。但是,在調(diào)研過程中,王維平也發(fā)現(xiàn)有些措施因為手段方面的原因還沒有達(dá)到人們預(yù)期的目標(biāo),垃圾的分類處理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報》就曾刊載過《垃圾應(yīng)該分類處理》的文章,但是因為階級斗爭而被迫中斷。中國是提倡垃圾分類最早的國家。如今,垃圾分類在中國與人們的預(yù)期還有不小的差距。”
2003年的一天,王維平早早地來到宣武區(qū)紅蓮小區(qū)進(jìn)行調(diào)研,這里是垃圾分類做得非常細(xì)致的典型社區(qū)。當(dāng)王維平翻遍了所有的407個垃圾桶之后,卻發(fā)現(xiàn)397個垃圾桶不是按桶外標(biāo)示倒的。王維平對小區(qū)內(nèi)的人們進(jìn)行了訪問,連續(xù)問了50個人對垃圾分類的看法,50個人的回答如出一轍:垃圾分類好啊,堅決擁護(hù)。垃圾的分類處理是一個任重道遠(yuǎn)的過程,預(yù)期和現(xiàn)實,認(rèn)識和行為存在明顯的差距。
王維平列舉了一組數(shù)據(jù),德國搞垃圾分類已經(jīng)8年,到如今仍然有17℅的人不按規(guī)矩倒,日本搞垃圾分類12年,到目前也有不少于10℅的人不按規(guī)矩倒。我國每年都在倡導(dǎo)垃圾分類處理,在垃圾分類處理上每年耗資幾千萬元,這的確是一件好事,但是卻涉及到一個手段的問題。當(dāng)我們的市民將垃圾分門別類地裝了數(shù)個袋子之后,垃圾車來了之后,一車端了,最后等于白分。如果分成九類垃圾,就要有九個車來拉,然后運(yùn)往九個不同的處理和利用場地。我們的城市垃圾當(dāng)今的最主要處理方式還是填埋,初期分得無論有多細(xì)致,最后都進(jìn)了填埋坑了。因此,我們要依據(jù)后端的處理和加工利用方式?jīng)Q定前端的垃圾分類。
王維平的垃圾對策的核心便是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在以王維平為首的一批專家的努力下,已越來越為國家和廣大的民眾所重視。200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huán)境防治法》已經(jīng)將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列為要務(wù)。今年,建設(shè)部157號令也強(qiáng)調(diào)了垃圾要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在這個過程中,王維平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給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現(xiàn)實可行性依據(jù)。
上世紀(jì)80年代末,北京垃圾圍城,通過對北京市區(qū)的三次遙感觀測,沿著三環(huán)路到四環(huán)路,發(fā)現(xiàn)大于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整個北京城區(qū)陷入了垃圾的重重包圍之中。今天,這種情況已經(jīng)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那么,曾經(jīng)圍城的那些垃圾去了哪里?
王維平是世界上對拾荒大軍進(jìn)行調(diào)研的第一人,也正在他的調(diào)研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了北京城市垃圾處理的一條龍的過程。“雖然政府投入了22億元,建立了數(shù)十個垃圾填埋坑,但是仍有一半的垃圾處理不了。而這些垃圾,都是被拾荒大軍撿走的。”
1988年,王維平給輾轉(zhuǎn)找到他的四川人許際才開了張條子,允許他在順義垃圾場撿垃圾,這是北京市拾荒大軍的最初力量。當(dāng)時許際才帶領(lǐng)500個人,每個人一個月能撿出1500元。一傳十,十傳百,許際才先后從家鄉(xiāng)帶來了2000多人到北京撿拾垃圾,最初的垃圾大軍初具規(guī)模。
拾荒大軍撿拾到的垃圾最后又大多數(shù)都運(yùn)往河北,塑料運(yùn)到河北文安、金屬運(yùn)到河北霸縣、玻璃運(yùn)往邯鄲、廢紙運(yùn)往保定、輪胎運(yùn)往玉田。北京的城市垃圾讓它周邊地區(qū)產(chǎn)生了產(chǎn)業(yè)活力。這些被熟視無睹的散落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們和那些令人掩鼻而過的垃圾儼然成了寶貝,盤活了很多產(chǎn)業(yè),也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yè)問題。
在《北京垃圾回收及產(chǎn)業(yè)化調(diào)研報告》中,王維平提出,都市“拾荒族”不應(yīng)當(dāng)是游離于政府視野之外的、不被社會關(guān)注的群體,不能讓這個產(chǎn)業(yè)無序地蔓延,應(yīng)當(dāng)讓垃圾回收成為一個在政府引導(dǎo)和社會關(guān)注之下的興利除弊的過程。報告一出,立刻引起了國內(nèi)外媒體的關(guān)注,政府也因此開始行動。
王維平的垃圾對策不僅僅關(guān)注垃圾本身,也涵蓋了對拾荒大軍的規(guī)范和引導(dǎo)。對中國的垃圾應(yīng)對現(xiàn)狀,王維平關(guān)注的只是和發(fā)達(dá)國家之間的差距,并一直為減小和發(fā)達(dá)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不斷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王維平不停地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和我一起做這個事業(yè),不停地去實踐,身體力行,使垃圾變廢為寶,為發(fā)展國家的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獻(xiàn)計獻(xiàn)策。”